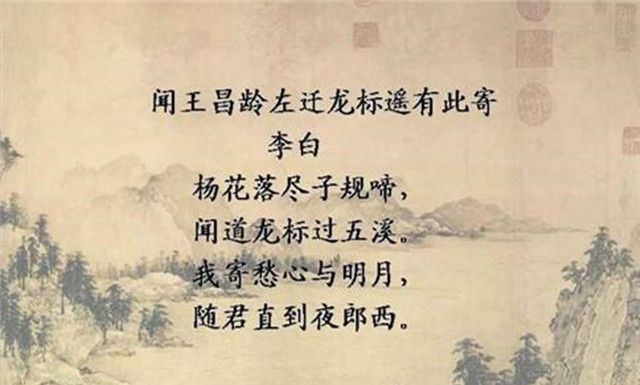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三十八》中,记载了怎样的一件秘史?
从谏如流:为啥孔僖议论先帝不被降罪反而升官

汉章帝刘炟在位时间只有十三年(公元76-88年),只活了三十一岁(《后汉书。卷三》记载为年三十三)。《后汉书》评价汉章帝善于识人,处事宽厚,在位期间,薄徭简赋,受到百姓称赞,并使边境稳固,各族和谐,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听得进各种不同的声音,能够从谏如流,也是一个政治开明的皇帝。有关汉章帝从谏如流的例子,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三十八》中,记载了下面这样一件事。
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鲁国人孔僖、涿郡人崔骃一同在太学就读,他们在一起相互议论汉武帝时,说:“孝武皇帝刚做天子的时候,能够尊崇信奉圣贤之道,可过了五、六年,就认为自己已经胜过文帝、景帝时期了。尔后,就任凭自己的意愿行事,而忘了从前的善政。”谁知这两个人对先帝的议论,被隔壁房间的太学生梁郁听见了。于是,梁郁上书告发,说:“崔骃、孔僖诽谤先皇帝,实际是在讽刺讥评当朝的时政。”这可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收到告状信的部门不敢怠慢,赶忙把这个案子交给主管的官员去审理。崔骃主动前往办案的官员处接受审查讯问,可孔僖却不去,而是向皇帝上书为自己辩解。他在奏章中是这样说的:“凡言诽谤者,谓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恶,显在汉史,坦如日月,是为直说书传实事,非虚谤也。夫帝者,为善为恶,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诛于人也。且陛下即位以来,政教未过而德泽有加,天下所具也,臣等独何讥刺哉!假使所非实是,则固应悛改,傥其不当,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数,深自为计,徒肆私忌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顾天下之人,必回视易虑,以此事窥陛下心,自今以后,苟见不可之事,终莫复言者矣。齐桓公亲扬其先君之恶以唱管仲,然后群臣得尽其心,今陛下乃欲为十世之武帝远违实事,岂不与桓公异哉!臣恐有司卒然见构,衔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后世论者擅以陛下有所比方,宁可复使子孙追掩之乎!谨诣阙伏侍重诛。”
这篇奏章虽然不长,但条理分明,铿锵有力。其文大意如下:凡称之为诽谤的事,是指实际并无此事,而是虚构加以诬蔑的。至于像孝武皇帝,其政治的好坏,己经明白地记载于汉史之中,就像日月一样坦荡。而臣下所议论的,都是史书上记载叙述的事实,不是凭空虚构的诽谤。凡为皇帝者,是好是坏,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因为他所治理的社会的优劣摆在那里,所以不能以此来惩罚诛杀人。况且陛下即位以来,政治教化没有过错,而对百姓的德政和恩泽却增加了很多,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臣下为何独要借古讽今呢?假使臣下真有什么对朝政的批评,如果批评得对,那就应当改过;就算是批评得不当,也应该包涵宽容,又何罪之有呢?陛下不去研究治国大略,不去为自己做深远的计划,只是大搞个人忌讳来使自己心意畅快。臣等受诛,死就死了,环顾天下之人,必将会因为此事反视反思,而改变想法,会以此事来窥探陛下的心思;从今以后,就是看见不对的、不可为的事,终将没有人再说话了。齐桓公能亲自揭露其先君的过错以问计于管仲,然后使群臣能尽心尽意,而如今陛下却想为十代之前的武帝来避讳很远的事实,岂不是与齐桓公的做法不同吗?臣恐怕负责审查的官员不问是非曲直来构陷臣下,使臣含恨蒙冤而不能自辩,这必将会使后世议论历史之人,随意用此事拿陛下来打比方,这也是无法让子孙来掩饰的一件事。现在,臣恭谨地前往宫阙,伏在坍下,等待重诛。
汉章帝看到这份奏章后,立即下诏停止对此事的审问,并任命孔僖为兰台令史(在皇帝和群臣之间行使“监察”和“上传”的职能)。
孔僖之所以能因祸得福,并不完全是因为奏书写得好,更主要的是因为汉章帝政治开明,胸怀宽阔,从谏如流,否则,孔僖就不会有这么幸运了。虽然孔僖的奏章写得不错,但其中有些话还是很刺耳的,譬如“徒肆私忌以快其意”,就是明显地指责皇帝大搞个人忌讳来使自己心意畅快,如果不是汉章帝能听得进不同的声音,孔僖还会有这样的幸运吗?因为在中国,无论是在皇家,还是在民间,都有“为长者讳”、“为尊者讳”的传统,特别是在皇家,更加避讳说先皇的不是。孔僖、崔骃议论汉武帝的不是,确实犯了忌,照常理,以大不敬治罪是跑不掉的。可以想象,如果孔僖不是犯在汉章帝手里,也许早就被杀头了,更别说还会升官。看来,汉章帝的开明也确实不是浪得虚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