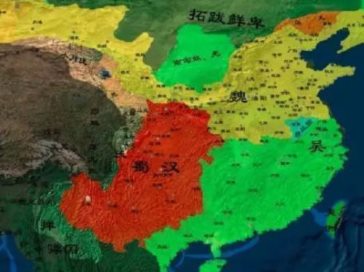俞大猷是谁:与戚继光齐名却被人们淡忘的英雄
对于英雄,遗忘远比非议更可怕。
嘉靖二十八年,四月。
廉州城外草长莺飞,城内人心惶惶。安南国(今越南)大臣范子仪领兵北上,在明帝国的南疆大肆劫掠,此刻正把廉州城围得铁桶一般。
大概是个傍晚时分,几名明军骑兵飞马自东而来,直奔叛军营地,即使持着使者旌旗,也有点过分的不可一世。“大明福建备倭都督指挥俞大猷有令,命尔等速速归降,否则不日天兵来到,将尔等化为齑粉。”
范子仪未必知道这个明国将领的名号,但看着使者倨傲的神情和咄咄逼人的威胁,感觉一支大军似乎随时会 在山的另一边随着太阳一起突然出现,于是集结军队,解围而去。
其实此刻,那位都督指挥的水军还未调集,而廉州已经告急。俞大猷用这次劝降争取了时间。等到一个月后,范子仪率兵突入钦州的时候,这支打着俞字旗号的水军,真的出现在安南兵背后,阻截战船、连日追击,斩首一千二百级,生擒主帅弟弟范子流,最后传檄安南国“杀范子仪函首来献,外患平息。”
水师 兵法,这是一次典型的俞大猷式的胜利。
与帝国的多数将领不同,这位福建泉州出身的武将身上,混合着一种允文允武的气质。俞大猷幼时家境贫寒,不仅要靠亲友资助,母亲还要编发网维生,但他依然幸运地接受了文、武两方面的教育。俞大猷曾经拜王宣、林福、赵本学等人为师,学习儒学、《易经》及由此推演出的兵法,武学则师从南少林高手李良钦,学习剑(棍)术和骑射。

受这种经历的影响,从戎后的俞大猷作战勇武而且善于运筹帷幄,把握战机,出奇制胜,在战略布局上的眼光也更为出众。在与倭寇的战争中,他指挥着曾不堪一击的帝国军队以奇谋妙计取胜,还总结出“倭奴长于陆战,其水战则我兵之所长”的战略特点,并由此建立起了一支以海军为主的“俞家军”。
大海是俞大猷的主场。以福建楼船为依托,俞大猷的部队创造了骄人战绩,战浙东、平浙西、复兴化,那些不可一世、甚至威胁过帝国旧都的亡命之徒,品尝到了毁灭的滋味,上百艘倭寇战舰在火光中沉入大海,数千名倭寇葬身鱼腹…想必,那战斗的场面绝不会比若干年后东北亚海面上的另一场大战——鸣梁海战逊色半分,而按理说,俞大猷和他的“俞家军”也理应成为朝鲜李舜臣一样的英雄,成为后世人提起”抗倭”时,立刻肃然起敬的一个名字。

然而,并没有。
与俞大猷相比,戚继光大概更加意气风发。
从登上历史舞台开始,戚继光就像一只斑斓猛虎,连额头上的斑点都闪烁着勇气和斗志。在龙山,上万精神萎靡的帝国卫所军在一千多倭寇面前丢盔弃甲,而这个英气逼人的青年将军,弯弓射箭,三声弦响,三名倭寇应声倒地,但凭借这精准的狙击便吓退敌军。
两军对垒万人众,唯有戚郎一男儿。骁勇果毅,是这颗帝国将星和那支追求绝对纪律、绝对勇气的戚家军最让倭寇丧胆之处。
与这个足足小他25岁的后生相比,久经沙场的俞大猷更像一条深藏的蛟龙。他在想着争取陆军一半的经费建设强大海军,在想着构筑连接海洋、海岸、内河、城镇的多层次防御纵深,在想着御敌于外的战略部署,甚至隐隐约约触碰到了改革帝国的旧有军制。
一个海上,一个陆地,一个骁勇善战,一个智谋广远,同样深得百姓拥护,同样让倭寇闻风丧当,拥有这对“俞龙戚虎”,本该让帝国高层感到幸运。而对于作战时间更长、参加战役更多、对倭寇打击更大,也是戚继光老师的俞大猷来说,理应得到同样甚至高于戚继光的地位和赞赏。
但是,并没有。
老成持重的俞大猷,在帝国体系内的另一场战争里连战连败,甚至时而一溃千里。这就是官场。
在帝国重文轻武的传统下,武官的战绩往往取决于庙堂小吏的刀笔,战将想获得晋升,就不得不依附于文官为主的 *** ,委身于官场的迎来送往人情世故。年轻的戚继光应该是深谙此道的,所以哪怕他心中如何无奈,如何痛恨,在绞杀倭寇之余,他总要找到些人情、祥瑞,随着谦恭至极的书信,上达天听,在功劳簿上打上条点缀的红缨带。
而俞大猷并不如此。也许是因为儒家道德的影响,也许是因为恃才傲物,这位性情耿直、为人正派的将领从不肯委曲求全,而只求实质性建功立业。所以有功无赏、赏赐不公、甚至被冒领军功就成了文官集团送给他的“常例”,平息安南入侵,严嵩将俞大猷的战功压下,只给了他五十两赏银,收复兴化,又是五十两赏银,非但如此,他的仕途动辄得咎,“四为参将,六为总兵,两为都督”的背后,是“七次屈辱,四次贬官,一次入狱”。
就这样踏步到了嘉靖四十二年,会打仗又会做人的戚继光已成了俞大猷的上司,俞大猷自己却还常常有免职之虞。
而最可怕的,是长久的历史中,同样出色同样英雄的俞大猷,也在慢慢消失在他的学生、好友、同僚戚继光的阴影下。
“借问浮云云不语,为谁东去为谁西。人生踪迹云相似,无补生民苦自迷。”晚年,俞大猷为晋江普照寺题写了四首“七绝”,这是其中之一。

命途多舛没有把俞大猷变成一个彻底的诗人。不管多少次被罚被贬,他都忍辱负重,光明磊落,坚持着“忠诚许国,老而弥笃”。去世前七年,他最后一次被免官,不久又获起用,最终病死任上。
他做过将军,为了保家卫国披肝沥胆,他留下了多部军事典籍,提出过保卫海疆的构想,做出过改革帝国军制的尝试,甚至试图收复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
他做过文人,戎马半生也未曾投笔,常与士人举行文会,教导他们学习《易经》,爱民爱兵如子,“为将三十年,不扰民一草一木”,以至于金门、海南百姓称其为“俞佛”。
他做过江湖高手,作为南派武学一代大家,留下了武学典籍《剑经》和一段少林授艺的佳话。
他甚至不缺历史花边,他的儿子驻防福建,被大海贼郑芝龙击败,而这个海贼的儿子之一,日后成为了名满中华的民族英雄郑成功。
但是历史正在遗忘他。
如果不加上“抗倭名将”的头衔,不加上“与戚继光齐名”的注解,不加上“和戚继光一样厉害”的解释,又有几个人知道这个现在听起来海鲜味十足的名字。
俞大猷几乎做到了那个时代价值标准下要求英雄的一切,立功、立言、立德,只是没有做到暗流涌动里要求的苟且,才让他生前事命运多舛,为文官集团打压侮辱,甚至身后名,都残存下了旧日暖阁里的幽灵。
倭寇早已荡尽,帝国也不复存在。明帝国肮脏而庞大的文官集团在塞北的鸣镝声中土崩瓦解,三百年后,另一个同样的文官体系也在外敌入侵中逐渐崩塌,这次的敌人正是来自俞大猷心心念念的海洋。
都过去了。笼罩在那个时代的丑恶也应该散尽,现代人再比较戚继光和俞大猷孰强孰弱,谁好谁坏已经完全没有了意义。只是当我们愿意以更公正的眼光看待前人时,愿意用先进的价值和标准回顾历史时,是不是应该给被埋没的英雄应有的位置,哪怕只是给他历史教科书上的薄薄一页,也足可以踩碎来自封建时代的恶毒诅咒,足以告慰英雄的在天之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