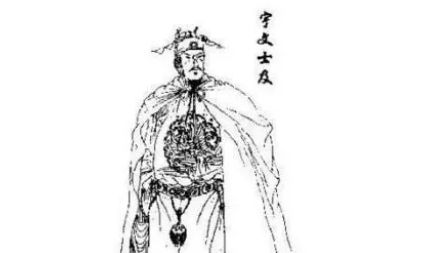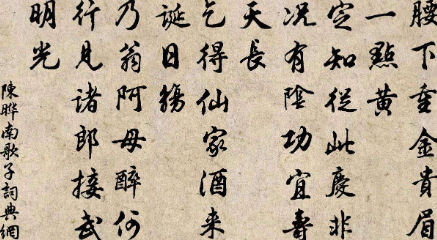柳宗元所作的《南涧中题》,将自己独特的人生感受融化进山水之中
柳宗元,字子厚,唐朝时期文学家、思想家,河东人,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文方面的成就大于诗。下面跟历史网小编一起了解一下柳宗元所作的《南涧中题》吧。
柳宗元从永贞元年贬谪永州,于此生活了将近十年之久。期间,他没有放任自流,而是甘于辛苦,“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新唐书》)寄情于山水,奋笔疾书,从而写成名流千载的游记体裁的散文名作《永州八记》,另外还有诸多诗作,比如《南涧中题》、《入黄溪闻猿》,等等。
山水诗蓬勃于南朝时期,自然环境对诗人作品风格的形成及影响,亦开始慢慢地受到诗论者的关注。正如刘勰在其《文心雕龙·物色》里阐述自己的理论:“屈平所以能洞监 *** 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此处的所谓“江山之助”,其实便是自然环境之客观物象对以审美经验和个人情趣为主体的诗人之相关感化。“情以物迁,辞因情发”(《文心雕龙·物色》),大抵如斯。
“山水雄险,则诗亦出以雄险;山水奇丽,则诗亦还以奇丽;山水幽峭,则诗亦幽峭;山水清远,则诗亦肖其清远”(朱庭珍《筱园诗话》)。
“游山水诗,永嘉山水主灵秀,谢康乐称之;蜀中山水主险隘,杜工部称之;永州山水主幽峭,柳仪曹称之”(沈德潜《说诗晬话》)。

对于自然环境对于柳宗元诗歌作品的具体影响,沈德潜已经注意到,并且给予了肯定适当地评价“幽峭”。在详细地比较了各种自然环境对几位诗人作品的影响之后,他另外强调了一点:“略一转移,失却山川面目。”时过境迁,环境固然可以适当影响着诗人的创作风格,但重要的还是诗人自身所具有的主观意识,而人的内部思想总是复杂多变的,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便是这个道理。
柳宗元山水诗作的峻峭风格,自宋及今,诗论家多有论述。根据后来者有心统计,其流传下来的一百六十多首诗作之中,被人评价为“幽峭”、“孤峻”风格的,大多来自于柳宗元贬谪永州、柳州时期的诗歌作品。
“柳子厚学陶,其诗刻峭,束缚羁絷,无聊之意,殊可怜”(方回《桐江集》。“柳州之诗,孤峭严健,无可拣择”(高斯得《耻堂存稿》)。“柳子厚清而峭”(胡应麟《诗薮》)。
明了此中关节,我们就会发现柳宗元的山水诗,其登山临水,写景抒情,绝不是刻意地静止地为之,而是熔铸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渗透了自己忧郁的情怀,将自己独特的人生感受融化进山水之中,以外在之自然山水来呈现内部之心灵山水。
《南涧中题》
[唐]柳宗元
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
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羁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
去国魂已远,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
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
诗题中之南涧,即是《永州八记》中《石涧记》之“石涧”,因其在永州朝阳岩之东南,故又称其“南涧”。《石涧记》写作于元和七年(812年),诗大约也作于同时。考量时间,柳宗元贬谪已经八年之久矣。
——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
秋之为气,宋人欧阳修在其《秋声赋》中如此写道:“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所以秋之衰败,实为眼前所见,然后心内所感,进而神意所会。此处用一“集”字,便带上强烈地主观感受,秋之为气何以能聚拢而汇集?也不能说完全是诗人的臆想,必须结合后面诗句参考详察一番才是。而后一句上首用一个“独游”,与冷冽秋气之汇集,根本就是相反的动作。此种无端之状况,便被此时一处鲜明的对比手法表现出来,愈加为我们显示出诗人境遇之孤寂与凄凉。正在于此,此后种种物象描写和情感抒发,便是基于如此一个“独游”二字之上。

——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
正所谓:“空穴来风,未必无因。”风之回也,一为自然之现象,一为诗人之主观。自从宋玉为《风赋》,分为“大王之风”和“庶人之风”,风便带上了浓郁地情感色彩,从此长存于文学史上。秋来万物萧条,风吹林木瑟瑟,在秋风无情地吹拂之下,树影晃动,高低参差,忽长忽短,恍若时光旅程,不知身置何处,心驰神往。回看开首两个诗句之尾有“亭午”一词,可知时辰为正午时分,原本午时为阳应该充满刚烈之气势,可是却因秋之故,只能于此承接“萧瑟”之破败。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底是天时变化之故,抑或是因人而异之由。不然,何必长久注视于树影的参差之态。
——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
初读此两句,大抵会放过其中深意,或以为便像句中所示之浅显意思:刚来到这里没有多久,我便能够有所体会,心中很是得意于自己的体悟,越深入其中就越发高兴,甚至因此而忘掉长途跋涉所带来的疲劳。前有秋气之衰败,回风之萧瑟,可以说眼中景物一片溃散之气象,诗人能够获得什么而使他忘掉疲惫?上下结合来看,便知其反话正说,亦可以理解为若无烦恼事,何来得解脱?固然明显说“忘疲”,其实于其内心深处何曾有半分之“忘”,所以才欲盖弥彰地申明“若有得”、“遂忘疲”。
——羁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
羁禽,不得自由之鸟,其声自当悲哀不可闻,散响于幽静而空荡的山谷里,更加令人闻之而色变。陶渊明诗句有:“羁鸟恋旧林。”或许,置身于无从适地位的诗人,内心里也当怀有如此心思。又《诗经·伐木》所写:“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诗人遭贬谪,可谓“羁禽”,故于幽谷鸣叫,其声凄楚,催人泪下,以求同伴,而友不至,只好“独游”。
晋陆机在《从军行》写道:“夏条集鲜藻,寒冰结衝波。”那么秋天山涧水流里的水藻,于此称之为“寒藻”,既可指当下气候之冷冽,然亦未尝不可指称诗人置身环境之恶劣。毕竟,其贬谪之地永州,在当时实为偏乡僻壤,甚少开化,多冷峭幽寂之景观。冷水之中,鱼已深潜,留寒藻独自舞动,“羁禽”之诗人,猝然目睹此景,不啻挨上当头一棒,心情当是更加怆然。回首上面之“忘疲”,此类转变实在是快速,可见诗人根本无法释怀,所谓“忘疲”本来就是一个假象。

——去国魂已远,怀人泪空垂。
因为有了上面各种景物描写做好铺垫,此两句便是水到渠成,方是诗人此时此刻的真情实感。事实上,不管是景物之萧条,得意之忘疲,其实都是衬托,好比一款背景墙,自始至终,昭示着诗人难以排遣的孤独,无法释怀的愤懑。“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无论离开京城有多么地遥远,诗人梦魂里牵挂着的仍是那一方土地;每当夜半梦醒时分,或者独自孤坐时候,他都会想念那些故人,并往往因此而泪流满面。诗人于此的悲痛,并不是为个人而伤感,他之感怀故人实乃建立在“政治”之上,是一种伟大的情怀。
——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
诗人如今恶劣之现实状态,皆由政治上的失意而引起,或许诸多感受,生存之孤独,生活之孤苦,生涯之孤寂,如此种种之“孤生”,都可能让他产生迷惘,不知身处何地之迷茫。扬雄《解嘲》有云:“当途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诗人之“孤生”大抵是因为政治上之“失路”,所以才有如前所述景物之荒凉意。这大约正是诗人此时之写照,真实而残酷,让他难以超尘拔俗,丧失掉当年的意气风发,变得毫无归宿之感,且如鸿雁失南北。
——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
前面曾写“忘”,实际上并非真正地忘怀,所以至此才又有着充满了矛盾地明知故问:现在这般萧索而落寞地生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样的事情呢?这样消沉地生活状态,只能加剧着内心的苦闷,所有这些彷徨无助都时刻提醒着诗人,不要忘记也不能忘记曾经的那些理念。所以,诗人身携此类复杂而繁琐的情感,身处逆境之愤懑不平,寻求解脱之悲哀抑郁,无处安身之徘徊忐忑,全部寄寓到眼前的自然景物之中。人道“情景交融”,诗人把一切情怀都物化到山水里面,让自己得以淋漓尽致地再现心灵困境,从而能够得以真正地获取情感上的某种升华。

——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
柳宗元在同一时期,曾写作《永州八记》之一的《石涧记》,其实便是记此南涧,其文写道:“交络之流,触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龙鳞之石,均荫其上。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得意之日,与石渠同。”文中言“得意”,提道后来者,诗中又说后来者,其身置于此,本是贬谪客,何以有“得意”哉?不外是学陈子昂之高呼:“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登幽州台歌》)诗人希冀的“当与此心期”之盼望,实际上乃是对同心同德者的等待,是一种困囿于失望之中的燃烧,是滩涂之浇薄里的幼苗,是“忧中有乐,乐中有忧”的情感包容与超越。
综观本诗,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到柳宗元永州山水诗作之脉搏,其虽然深意于“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之特殊境界,神与物游,不断强迫自我陶醉于自然物象之绚丽多彩中,可是其蕴藏心底之文化内涵和胸怀之政治抱负,却总是在其登山临水之际涌上心头,与其隐含着的迁客逐臣之孤寂愤懑杂糅交汇。此种相互对立之情绪如恬静与孤寒,闲散与寂寥,轻快与抑郁,在凄清、幽寂、孤峭的自然环境中,反而更能让人深刻体味出来。正如明代茅坤所论:“五岭以南,多名山削壁,清泉怪石。子厚与山川始两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亦无以发子厚文。”(《唐宋八家文钞论例》)此论虽然是着眼于其山水游记之文章,但此处用来评价其写作于永柳两州之山水诗,却也是非常适合且恰当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