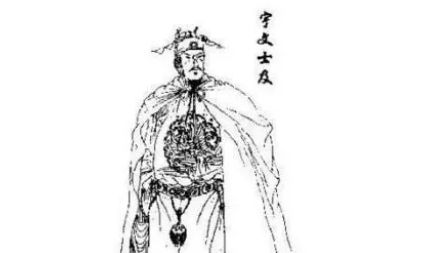血染红楼:残绝绣橘悲诉迎春惨状!!
沉默半晌,鸳鸯道:“我想还是先瞒着老太太,等大老爷和琏二爷办妥了,过后再慢慢告诉。”凤姐道:“说说倒容易,如今老太太已听见些声了,怎么瞒过去?我是没了主意,你倒说个法子。”鸳鸯明知凤姐是故意推脱,好让邢夫人怪不了他。虽然自己与邢夫人有过节,但如今凤姐不管,少不得只好自己出头。因此想了一想,道:“如今只好这么办了。”凤姐听了道:“也罢,要问起来,就依你的主意办事。”又嘱咐了绣桔一篇话,自己同着鸳鸯先进去了。
贾母便道:“怎么去了半日,究竟何事吵吵嚷嚷的?”鸳鸯便道:“老太太,也没甚大事,只是孙家来人说,二姑娘病了,请了几个太医都看不好,便来请大老爷和琏二爷过那府去。”贾母道:“那有什么好吵的?”鸳鸯道:“不是吵,是绣桔这丫头糊涂,只管跑了来胡闹。”贾母纳罕道:“绣桔又来闹什么?”鸳鸯打量着贾母的脸色,道:“他素日和二姑娘亲厚,见他姑娘病了这些日子,又没个好医生,心里一时着急,也是怕老太太不看重的意思。”
贾母听了,果然有些不自在,便向王夫人、薛姨妈等人道:“真真这个丫头糊涂!我的亲孙女,我怎么不看重。自他出嫁后总未听你们提起来,上次回来还是上年的事了,也只匆匆忙忙的让我见了一面,话儿也没说上几句。我虽老糊涂了,心里头还是时时记挂着这些孙女儿们。那天我还问起迎丫头来,听你们说他在孙家很好,我也心里受用,当初就怕嫁个不如意的人家,委屈了他。这孩子从小就老实,可怜见儿的。”薛姨妈忙赔笑道:“老太太说的是。”贾母又向邢夫人道:“如今既然病了,传我的话,即刻叫你大老爷和琏二爷带上府里四个太医过那府去,好生诊治了,还叫迎丫头安心养病,不用疑神疑鬼的。年轻轻的,有什么大不了的病?”邢夫人忙应了一声,起身出去了。鸳鸯早又把王夫人也请了出去。
这里绣桔见邢夫人和王夫人出来,扑通一声便跪下哭叫道:“太太!姑爷,姑爷他——”邢夫人道:“怎么,姑爷有什么不好么?”绣桔哭道:“姑爷不是人,分明是一头恶狼!活生生把二姑娘——打死了!”邢夫人、王夫人听说吃一大惊。鸳鸯忙搀绣桔起来,说道:“有什么话还是到太太屋里说去,这里仔细老太太听见了。”于是一群人便往邢夫人院里来。
绣桔声泪俱下:“自姑娘过门儿到孙家,开始不过小吵小闹,骂姑娘几句,气得姑娘哭几日也罢了。后来试着姑娘好性儿,他便一步一步越发得了势,凡事不论青红皂白,先劈头盖脸打了骂了再说。姑娘过门儿才一年,浑身上下竟无一点好处。那几日姑娘滴水未进,粒米未沾,又受歹话,又遭毒打,病得抬不起头来,他竟不让请大夫来瞧。昨儿只因一句话姑娘答应他慢了些,他便暴跳如雷,说姑娘有意怠慢他,也不管姑娘正病着,竟丧心病狂的把姑娘从病床上拽到地下,把我推到屋外,不让我跟姑娘在一起,他自己竟锁了门出去了。后来我拼着一死撞开了房门,可姑娘已经咽气了。太太,太太,你们一定要替姑娘作主申冤,报仇啊。”
听了绣桔这番言语,众人早已哭作泪人儿一般。迎春本非邢夫人所生,邢夫人原也不疼他,不过是情面难却,又有许多人在这里,也只好用手帕子使劲儿把眼睛揉红了,挤出几滴泪来,说道:“迎丫头是孙家的人了,俗语说的‘出嫁从夫’,我们好怎么样呢?”绣桔反诘道:“难道姑娘就白死了不成?”邢夫人一时语塞,脸色便难看起来,冷笑道:“你原是陪嫁丫头,姑娘过门儿,就是交给了你,你在那里是作什么的?”绣桔咬牙道:“我能做什么?”因把袖子撸起,胳膊上全是一条一条淤痕。邢夫人便不言语。
鸳鸯忙劝绣桔,又道:“太太,自古打死人就要偿命的,不能因为孙家和我们是亲家,就不管。”邢夫人听了道:“我何曾说过不管了?罢!叫大老爷过去,了结完事。”又说:“叫人送了这绣桔姑娘回去。”绣桔道:“我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那恶狼的下场。我要亲眼看着太太替姑娘申了冤我才回去。”鸳鸯也道:“绣桔还是暂留在这里好,分明看着那是虎穴狼窝,何苦还把人往火坑送。回去了,那孙绍祖未必会放过他的。求太太开恩,留他住几日,待事情调停解决妥了再回去不迟。”王夫人也说:“绣桔就留下罢,事情闹到这样,也说不得什么娘家婆家的话了。”
邢夫人先听绣桔当众一句锋利的诘问,已是窝了一肚子火,又听鸳鸯如此说,心里早又不大自在,又碍着王夫人在这里,且王夫人也留他,不好发作,少不得忍了气说道:“也罢,就留下。着人收拾停当了饮食住处。”又有人来回说:“已请了大老爷和琏二爷过那府里去了。”邢夫人只点头说:“知道了。”也无多话,只叫丫头过来伏侍休息。王夫人等不便久留,便散去了。邢夫人见人走了,便啐道:“呸!鸳鸯小蹄子越发得势上脸了。还有那琏儿媳妇,也弄不清自己是那一房的,只管跟着那一干人压我的势。终究我要争回这口气!”于是一气之下,竟将绣桔硬逼回了孙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