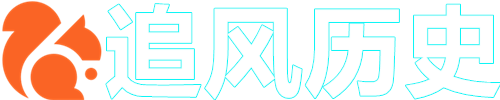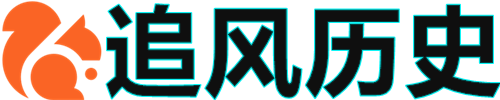成吉思汗后裔,改名换姓各自逃命,600年后,靠一首诗团聚四川
文| 赤晚
编辑| 赤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诗词耳熟能详,但大家对于成吉思汗本人却并不是特别了解,蒙古族人,居于草原向来传说颇多。
因为神秘,所以探寻者历来层出不穷。
尤其是,近年来关于“黄金家族”的新闻多如牛毛,成吉思汗后裔历时600年重新聚首,着实奇幻。
媒体记者为了截获之一手资料,纷纷前往四川,所求之答案竟是一首诗。
那么这首诗从何而来,又讲述的是什么呢?


一家分作万千家
在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余家湾村,生活着众多的余姓后人,他们与一般 *** 看上去并无不同。
但是,他们却言称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为防人们不信,几乎家家户户都印有《族谱》副本。
消息一经传出,便迅速引起了国内专家们的关注,毕竟大家对于成吉思汗的名号莫不是如雷贯耳。
他建立大蒙古国享誉中外,率领蒙古铁骑南征北战,是蒙古族当之无愧的大英雄。
但再是响亮的名号都阻挡不住岁月的侵蚀,子孙建立元朝统治,不过百年时间沉溺在历史长河。

据余家湾人叙述,他们所提及的先祖就是成吉思汗的五世孙铁木健,骁勇善战,在当时可以说是功勋卓著。
《余氏家谱》中记载:“我祖铁木健,系元成宗皇帝铁木耳之二弟,初封南平王,食邑湖广麻城……”
受到朝廷重用的程度可见一斑,但也正因为如此,不免就招惹来了一些小人嫉妒,暗中加害的心思一日比一日强烈。
时值元顺帝执政期间,他大兴土木,偏听偏信毫无主见,民间“红巾军”闹腾的厉害,江山安稳颇有些严峻。

元顺帝莫不将其视作眼中钉、肉中刺,佞臣借机夸大其词,言称铁木健暗中联合了“红巾军”意图谋反,他如何能忍。
对于自己的执政能力,元顺帝想必是心知肚明,心中担忧是肯定的,竟真的对护卫疆土、忠心耿耿的铁木健生出了猜忌之心。
想来这也并非一时兴起,铁木健深得人心,家中人丁兴旺,若是真有此意,莫说就不能取而代之。
终究是功高震主,难有善终。

铁木健为官多年,虽说出门征战的时间更长些,但他在朝却也是耳目众多,单是家里人就足有十位之多。
“九子十进士”说的就是铁木健一家,九个儿子高中进士一一入朝为官,就连唯一的女婿亦是如此。
如此人脉也难怪上位者放心不下,有能力就是他的原罪,铁木健敏锐的察觉出了元顺帝的心思,主动上书请辞。
这不失为明智之举,但元顺帝安能放他一族全身而退,何况民间政权纷争,新朝一朝建立,想来也不会放过铁木健一家。
北方故土难回,一路南逃直入西蜀。
铁木健虽说走得果决,但旧主的不信任终究还是令人心伤,再加上一路舟车劳顿,年事已高的他在逃亡途中离世。

铁木健的后代一路行至泸州凤锦桥处,后面的追兵依旧不断,一大家子人连带着行李颇为惹眼。
化整为零当是逃命的更佳方式,于是铁木健的九子一女插柳为记,题诗为证,咬指作笔,以血代墨。
“我本元朝宰相家,红巾冲散入西涯。泸阳岸上分携手,凤颈桥边插柳丫。 否泰是天还是命,悲伤思我又思他。十人失散之何处,如梦云游浪卷沙。余氏并无三两姓,一家分作万千家”。
按照长幼顺序,一人一句遂成“接头诗”,大家都是血脉至亲,后代若是有缘相逢,当是此十人后代。
改“铁”为“余”,兄妹十人自起姓名,有相关记载表明这是取自“杀不尽、斩不绝,还有余”之意。

可改姓并非小事,历史上关于“余姓”的由来有很多个传说。
一种说法是铁木健后人当时逃亡路遇大河,河中有鱼将他们渡过,遂改姓氏加以感念。
还有说他们逃亡途中路遇关卡,指鱼为姓方顺利通关,另有一种传言指当时追兵追至河边,众人躲在桥下,声响不断皆归鱼身……
其中,1890年版的《余氏族谱》记载:“凤锦桥边,鱼渡过津,先改铁为金,腹痛难行,金去下一,姓余得生。”
虽说有些神话意味,但莫不说明“余”姓是铁木健子孙深思熟虑之举动,姓名重新改过,各自逃命为要。

四川、云贵、泸州、犍为……十人带着各自的家眷开始逃散,本以为很快就可以进行联络,奈何外面风云变幻不断。
明朝初年,朱元璋对于元朝贵族的追捕力度相当之大,众人只好继续隐姓埋名,不敢轻易暴露。
来到余家湾的这支队伍同样蛰伏不出,换上了当地的服饰,藏起了祖辈的弯刀,有模有样的学起了耕种。
他们不敢与各地的亲人取得联系,只能将临别之际写成的那首诗代代相传,期盼着有一日能一家团圆。
后朝代更迭,人们四散,社会动乱,战事惨烈,山中不知岁月,眨眼之间几百年就过去了。
直至新中国建立,余家湾村的人才开始有了寻找亲人的行动,但去向不明,模样不识,无异于大海捞针。


盛世聚首代代传
“我本元朝宰相家”请接下一句。
余家湾村人将“接头诗”的之一句登在了当地的报纸上,可是左等右等没有等来自己想要的答案。
倒是有一些古诗词爱好者争相接话,可这并不是余家湾村人的本意,想来找人不能只局限于四川地区。
继续扩大范围找寻,所有族人都在等待着回音,不期然的有人成功接对,顺着地址找到了余家湾村。
这里风景秀美,确实是个隐蔽行踪的好去处,放眼望去,20多户人家的眼中都是殷殷期盼。
大家和 *** 生活早已融入,过着一样的节目,拜着一样的神明,祈求风调雨顺,来年丰收,这里与世隔绝,就是现世的“方外之地”。

等到来人上门,余家湾村人很是欢喜,两方落座细数先祖功绩,往上一直追溯到泸州凤锦桥处。
当年四散的两支队伍成功相聚,都是成吉思汗的后人无疑,看来“大海捞针”的 *** 还是有些用处的。
找寻亲人的队伍就这样不断壮大,铁木健九子的后裔接连现身,虽说此前是陌生人,但说起先祖往事个个滔滔不绝。
《余氏家谱》几经修订,族中研究者更多,搜集文献跑遍了蒙古国余姓族人所在之地,开始筹办聚会。
可不管是多次在四川举办的铁改余联《谱》、还是2002年在云南曲靖召开的《续谱》,都未见有铁木健女儿的后代。
这不禁让人心生担忧,众人盼望着亲缘团聚,随之不断找寻,沈村余姓大族开始显露在世人面前。

他们对于先前的聚会一概不知,经有关人员考证,沈边长官司铁改余姓蒙古人确系就是成吉思汗的后裔。
《四川通志》和《余氏家史》都随之证实了这一点,对于先祖留下来的“接头诗”亦是对照无误。
当初四散的十支队伍重新聚齐,着实不易,经由社会动荡,余姓后人只增不减,想来与当时逃离所携带的男丁家眷有关。
落户繁衍,代代埋名求生,成为了各地有名的望族,虽说没有完整的身份,但性命尚存,一切就皆有可能。
有蒙古人铁木荣被国务院批准恢复身份在先,各路余姓族人纷纷加入身份证件的修改大军,改汉族为蒙古族。

2009年,成吉思汗二十九世孙阿拉木萨前往四川探亲,和余姓族人畅谈古今,交流越深感情越是亲近。
随行的电视台及时报道了这次见面,令无数蒙古族人感到有荣与焉,他们开始逐渐的恢复了蒙古节日。
身着隆重的蒙古服饰进行庆祝,手拉手欢歌起舞,因为有着共同的先祖,有些脾性总归是有些相似的。
“黄金家族”的队伍不断壮大,知道自己身份的蒙古族人纷纷前往四川,手中皆有信物为证。
不禁令人感叹,历经几百年岁月、几代人的临终叮嘱终有了如今欢聚一堂的盛景。

2022年4月4日,成吉思汗后裔铁改余第五届清明祭祖大会在崇州顺利举办,与会人员来自四面八方。
各分支代表全部到齐,一同祭奠先祖,当地的余氏祠堂大门敞开,上香、叩拜仪程完整。
典礼过后,相熟的人们开始畅谈近况,生活安稳、交通便利,大家往来的机会逐渐增多。
后代绵延不绝,“接头诗”依旧代代传颂,这都是历史的见证,在最初验证身份时,就有专家发了言。

当初蒙古武力建国,被统治者派遣到全国各地驻扎的族人众多,后朝代更迭,谁都不敢保证全部的蒙古族人都撤回到了科尔沁草原。
余姓族人十支分散,如今找回是幸事,可依旧还有众多不明身份的蒙古族人在与世隔绝的生活着。
年代久远,想来他们生活的早与 *** 无异,若是没有凭证和遗嘱,想来认亲的道路艰难,其中不乏无意修改的人们。
但不管怎么说,当初铁木健的九子一女后裔终是聚首,当初创作的那首诗也变得脍炙人口。
蒙古族人寻亲的队伍还在壮大,虽说历史难以更改,但创造新的历史未尝不可,本是同根生,就应同进退。
参考资料:知网《成吉思汗的后裔在泸定?(上)(下)》
《西南余姓家谱中的神话及传说探究》